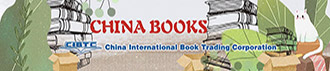以草木喻人書寫鄉村變遷
發布時間:2024-05-24 09:01:24 | 來源:人民日報海外版 | 作者:老藤 | 責任編輯:孫靈萱老藤
屈原在《離騷》中有這樣一句:“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珵美之能當?”大概意思是連草木都分辨不得,更談不上去鑒賞美玉了。這是屈原的自謙,屈原喜歡以香草喻君子美德,他對草木的認識是深刻而獨到的。《離騷》中寫了許多香草,如江離、芷、蕙、蘭、留夷、揭車、杜衡、菊、荃等10余種。了解如此多的品種,對今天的作家來說是極高的挑戰。學習《離騷》時,為了弄清詩中的香草,我一遍遍查閱資料,雖然辛苦一些,但也甚感樂在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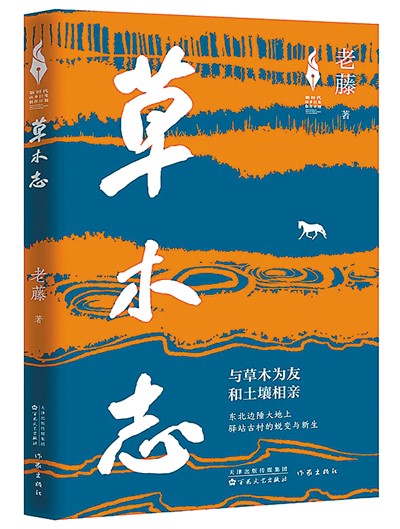
我對草木有一種天生的親近感,這大概與我在北大荒的濕地邊生活過有關。濕地是植物的王國,一個人只要少年時在濕地周邊生活過,草木和繁花就會成為記憶的底色,每每見到綠植,我就會像邂逅故友一般心情愉悅。我有個習慣,見到陌生的草木總愛刨根問底弄個明白,手機里拍照識草木的軟件利用率極高。只要有時間,對那些熟悉的草木,我也喜歡反復觀察,每次觀察都會有新發現,可謂“覽察草木皆有所得”。與人相同,草木也在成長,不同的季節,草木呈現的精神氣質會有所不同。比如對牽牛花的觀察,就讓我有了些哲學思考。清晨,牽牛花在太陽尚未升起時就開始笑臉盈盈,像運動會上期待檢閱的孩子。太陽升起后,一上午它都像微縮版的葵花一樣目不轉睛地仰望紅日。但只要正午一過,它就會馬上斂起笑容,收攏自己,將敞口的喇叭縮成一截花棍,悄悄隱藏在蔓葉間不再露頭。牽牛花對西墜的太陽變臉如此之快,讓我百思不得其解,它是靠什么區別12點的太陽與13點的太陽?換言之,相差一個小時,陽光能有多大區別呢?但牽牛花區分得絲毫不差。我曾戴著遮陽帽,坐在馬扎上觀察小區里的牽牛花,小東西簡直神透了,到點就收工,絕不拖泥帶水,而且收工速度極快,太陽明明還在肩頭掛著,小東西竟然隱身不見了。
毫無疑問,對草木的喜愛是我創作《草木志》的動力所在。《草木志》最初叫《依依墟里煙》,由寫炊煙入手來寫鄉村的變遷。寫炊煙的時候自然會聯想到作為柴禾的草木。鄉村的炊煙之所有五色五味之分,是燃燒的草木不同所致。比如干透的柳枝,燒火做飯只有少許白煙,被初升的朝陽一照,白煙會鑲上金邊,發出耀眼的金色。又如干透的麥秸,在鍋灶里燃燒時會散發出甜味,而大豆秸燃燒時不僅噼啪爆響,而且會散發出誘人的油香。用不同的柴火熬出的菜、燉出的肉,味道差別不小,有經驗的村民,一口便會吃出你做飯是燒的什么柴。墟里人是不屑于燒煤的,因為煤火燒出的飯菜沒有味道。這些真實的感受改變了我最初的想法,干脆寫一部《草木志》吧!就這樣,《依依墟里煙》變成了現在的《草木志》。

老藤近照
《草木志》用34種植物命名章節,這些植物都屬于東北,屬于大小興安嶺。34種植物各自對應一個人物,在小說中人與植物是命運關聯體,他們在精神上緊密交織在一起。當然,這種關聯本身也在變化,有的人由最初某種草本植物,后來“變成”另一種木本植物,這是生活的可塑性使然。其實,世界上沒有什么會一成不變,人也好,植物也罷,變化才是常態,人要把握的是變化的走向,從而趨利避害。小說中寫了一個叫“老堵頭”的人,他對應的植物是狗尿苔。狗尿苔是一種菌類,一般生長在樹木根部。在老百姓眼里,狗尿苔是爛命一條,很低賤。一般人認為狗尿苔有毒,不可食用,真實并非如此,狗尿苔的前半生是無毒的,可以放心食用,只有當它的傘蓋變黑之后,才會變成有毒的菌子。而“老堵頭”在進監獄前是一個任勞任怨的糧庫職工,為人也不錯,稀里糊涂成了罪犯后他變得不再善良,獨自跑到江心島上過起了與世隔絕的日子,他給“石鎖”出的壞主意——用滾鉤割碎江汊子的養殖隔離網,可謂陰險毒辣。那么,“老堵頭”為什么會變成帶“毒”的狗尿苔,這恰恰是應該思考的問題。我在小說中表達這樣的認識,社會一旦失去公平正義,一切就會扭曲變形。在鄉村全面振興過程中,必須讓每一個鄉親都能享受到政策紅利,感受到社會的公平,唯有如此,狗尿苔才會變成人畜無害的食用菌。
草木蔓發,春山可望。作為一個從鄉村走出來的文學工作者,我經常思考全面振興后的鄉村應該是何種樣貌,是樓宇林立、廠房遍地,還是安居樂業,草木葳蕤?不得不說,我更喜歡的鄉村景象是具有田園風的后者。將農村城市化,對于城市周邊的村屯也許是最佳選擇,但不是唯一路徑,“千村千品”才對,千篇一律就有些簡單化了。只有將產業、生態、文化和人才等諸要素合理擺布好,鄉村功能才能健全,鄉村發展才可持續。有的地方熱衷于另起爐灶,大范圍異地重建,導致傳承不再、村脈中斷,這是不可取的。我們不妨從草木生存之道上尋找一下參照。大山絕壁上經常有崖柏、野杜鵑、蘭花、不老松等植物,它們在石縫里生存極為艱難,似乎怎么長也長不大,但千百年來它們一直以自己的姿態活著,見證著四季輪回。有人好心把它們挖回來,栽到院子里或花盆里,施肥、澆水,悉心照料,結果成活率極低。一方水土養一方草木,水土異,味不同。草木有道,道法自然,不能拿一把標尺去度量蕓蕓眾生,萬物皆有所待。因地制宜、不違自然之道,鄉村全面振興才會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草木志》中的墟里是古驛站的活化石,是300年前雅克薩奏捷之路的見證者,在合村并屯大趨勢下,是把它從地圖上抹去,還是激活它的內生動力、讓它繼續活下去?這是墟里人面臨的大問題,也是許許多多古村落同樣面臨的問題。在這種情形下,上級扶持政策給墟里打開了一扇別開生面的窗子。駐村干部“我”因為對這個古村的喜愛和對這個植物王國的情有獨鐘,開始做起“有形之事”。當然,“我”深諳“墟里的事最終要靠墟里人來解決”的道理,沒有越俎代庖,而是想方設法把本村喇叭匠“哨花吹”扶持起來。“哨花吹”是個具有農民智慧的民間藝人,他不想一個300歲的古村就此終結,更不想村民們百年之后成為進不了小龍山的“孤魂野鬼”,于是帶領村民消弭前嫌,合力發展文旅融合產業,讓墟里實現了魂體相依,恢復了郁郁蔥蔥的生機。
《草木志》以草木喻人,隱含著我對鄉村空心化的擔憂。鄉村靠什么留住年輕人?年輕人在鄉村如何實現自身價值?鄉村的未來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組織形態?這些都是社會學家要思考的問題,身為作家,我只能通過墟里的復活提供一個參照而已。草木繁茂的墟里讓人欣慰,有被“驛路遇見”文旅融合項目吸引而來的年輕人,有保護良好的森林濕地,還有原生態的驛路民俗,這種屬于鄉村的樣貌讓墟里顯得更加可近、可親和可愛。
其實,鄉村與城鎮是互促互進、共生共存的關系,二者共同構成人類活動的主要空間。不要總想著一方化掉另一方,和而不同,相互依存才是傳統文化中的君子之道。小說中我不可能闡釋政策,但我沒有回避信息時代鄉村應該傳承什么、守護什么這個核心問題。雖然墟里人做到了,但在現實生活中有些困擾依然存在,鄉村的命運和未來仍然是一篇需要用心書寫的大文章。
(作者系中國作協主席團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