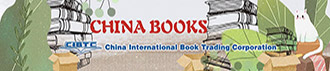老舍:致力于東方與西方的“相遇”
發布時間:2024-08-16 09:24:23 | 來源:光明日報 | 作者:鳳媛 | 責任編輯:孫靈萱【追光文學巨匠·紀念老舍誕辰125周年】
作者:鳳媛(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老舍研究會副會長)
今年是老舍先生誕辰125周年,文學界舉行了不少紀念活動。每每置身其中,我都在想,老舍離開我們快六十年了,他的作品為何還能被不同地域、不同領域的人們,以各種各樣的方式追憶和復現?為什么老舍的人與文在歷經歲月風塵后的今天仍舊可以熠熠生輝?當我們在紀念這位文學巨匠時,我們到底在紀念他的什么?

老舍(1899—1966)資料圖片
1.傾情“小人物”,踐行“靈的文學”
老舍一直秉持寫“小人物”、為“小人物”發聲的創作品格。這些小人物不僅指他們是身處底層、物質上困窘的貧民,還包括那些在社會中籍籍無名、微不足道甚至是生活的失意者和失敗者。1899年,老舍出生在北京西城的一個貧苦的旗人家庭,“我昔生憂患,愁長記憶新。”這時正值清政權走向窮途末路,顯赫一時的八旗階層也日漸衰微。相較于同時代作家,老舍的世紀末情緒因為他的末世旗人身份更多了幾分哀傷與悲情,這也給老舍提供了一條和那些小人物相融無間的情感通道。
他的《離婚》《駱駝祥子》《牛天賜傳》《我這一輩子》《月牙兒》等作品,將筆觸瞄準城市中的普通市民,寫他們的艱難生計和辛苦境遇,寫他們被生活逼迫到走投無路,卻對“為何如此”和“應該怎樣”始終懵懂和茫然。寫于抗戰時期的《四世同堂》,塑造了淪陷區底層社會的人物群像。小羊圈胡同中,既有從與世無爭的“順民”最終走向“硬正”和反抗的老一代中國人祁老太爺、錢默吟;也有心懷正義,卻又在“救國”還是“保家”、“盡忠”還是“盡孝”之間徘徊,以祁瑞宣為代表的年輕一代。老舍很少對這些小人物進行一種善惡忠奸、非此即彼的符號化和標簽化處理,而是通過時勢造就、文化因緣和個人境遇等因素,解釋他們處境的來龍去脈、是非曲直。這種洞明世事的犀利眼光,成就了老舍筆下一系列經典的人物形象,也為我們思考當下的創作應該如何關切書寫對象提供了啟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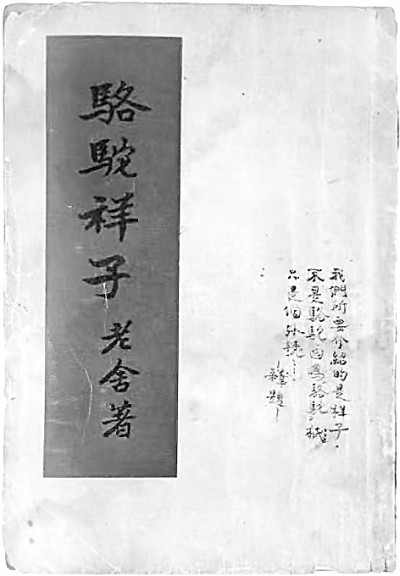
1939年《駱駝祥子》再版資料圖片
與寫小人物密切相關的是老舍對于“靈的文學”的追求,也就是在創作中著意對人心和人性之復雜幽微的開掘。“靈的文學”是老舍在1941年一次演講中的一個提法,他認為但丁的《神曲》是“替西洋文藝開辟一塊靈的文學的新園地”,而在當時的中國“確實找不出一部有‘靈魂’的偉大杰作”。因為他們的創作都太過矚目于現世和肉身,所以他呼吁要推動“中國靈的文學,靈的生活”。這種“靈的文學”的追求并非一時興起,在他的創作逐漸走向成熟的20世紀30年代,這種趨向就已經體現得十分明顯。
以《駱駝祥子》為例。在這部小說的閱讀史中,祥子“三起三落”的命運悲劇,極易只被解讀為黑暗社會對底層生命的無情傾軋。兵匪、偵探等利爪在相當程度上確實造成了祥子幾次丟車的命運跌轉。但細讀文本會發現,老舍創造祥子的形象不只是簡單地批判黑暗社會。小說沒有明確標識故事發生的時間,老舍對小說的時代背景明顯進行了一種模糊化的處理。在談及這部作品時,他說:“我所要觀察的不僅是車夫的一點點的浮現在衣冠上的、表現在言語與姿態上的那些小事情了,而是要由車夫的內心狀態觀察到地獄究竟是什么樣子。”也就是說,老舍希望寫的是祥子的內心世界及其背后的心理動因。由于對車夫內心狀態的關注,老舍將祥子塑造成了一個木訥寡言,卻有著極為豐富內心戲的人。祥子每次命運轉折的關口,都有他在實現志愿、欲望和自我道德要求之間,成為“超人車夫”和行尸走肉之間的反復辯駁與較量,并最終導致了他的行善或行惡。這部小說寫出了小人物的一段靈魂墮落史,表面波瀾不驚,內里卻驚心動魄。在祥子自苦式的個人奮斗之路中,不斷要求上進和受到挫折后的自我懷疑,備受壓制的欲望和被點燃之后無法控制的泛濫,在欲望中的沉淪和在道德反省中的掙扎,都是具有普泛意義的人性追索。2024年年初,國家話劇院導演方旭將《駱駝祥子》搬上話劇舞臺,吸引了大量不同年齡、職業和身份的觀劇人群。我想,他們應該是在祥子痛苦糾結的靈魂之旅中也瞥見了自己人生成長中的某些瞬間。

1946年《四世同堂》初版本資料圖片
2.文化批判的眼光不僅是極具穿透力的X光射線,更像是一座燈塔
老舍創作中還有一個很鮮明的特色,那就是立足于人的合理生存的文化批判意識。
1924年,他到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學院擔任中文講師。英倫五年的經歷,讓他深切體察了這里的國情與民情。他借小說《二馬》,“比較英國人和中國人的不同處”,同時“更注意他們所代表的民族性”。小說中的老馬父子遠渡重洋到英國繼承老馬哥哥的古玩鋪子,他們不僅感受到英國人作為現代社會國民的不少優秀素質,更體會到普通英國人對中國人種種妖魔化的誤讀。老馬身上未老先衰、不思進取、庸俗無聊的精神狀態固然值得批判,但小說又通過英國房東溫都太太的視角,寫出了老馬講禮數、重人情的性格特點。故事發生在20世紀20年代的英國,正處于一戰后的修復期,這個國家的物質基礎已經千瘡百孔,英國人之前趨于統一的價值和信仰系統同樣經受了巨大摧毀而漸近潰散。同時工業革命所產生的一系列現代性后果又逐漸顯現,人們被金錢規則和工具理性異化得如同電影《摩登時代》里的人物,加之民族偏狹主義的有色眼鏡,種種因素讓小說中大部分英國人既顯得傲慢狹隘,又空洞無知,處在一種被審視的位置。
老舍借助中英兩國人物之間的互視,實現了一種雙向的文化批判,既看到中國和英國國民性中各自的短板,也能在互相審視中看到彼此的優長。老舍始終沒有忘記文化批判的思路,他感到越是在戰時的特殊境遇下,傳統文化的弊端和優點也會凸顯得越加突出。他說:“戰爭給文化照了‘愛克斯光’。”又說:“一個文化的生存,必賴它有自我的批判,時時矯正自己,充實自己;以老牌號自夸自傲,固執的拒絕更進一步,是自取滅亡。”

老舍生前居住的小院。資料圖片
最終在美國完成終稿的《四世同堂》,近年來被挖掘并回譯出失而復得的最后十余節。這些內容表面上看是錢默吟的“悔過書”,但實際是老舍在后抗戰時期對戰爭和文明、文化的集中反思。他想追問的是:人在什么樣的文化中才能夠更加合理地生存?這種文化批判的眼光,不僅是極具穿透力的X光射線,更像是一座燈塔,觀照出幽深駁雜的世界文化圖景和深邃的人道主義精神。
3.“我們自己也是世界人,我們也是世界的一環”
老舍是一個地方色彩很強的作家,是京味兒文學的杰出代表。北京之于老舍,既是生于斯長于斯的故鄉,也是他文學創作依賴的靈感沃土,但這并不意味著老舍只是“北京的老舍”和“中國的老舍”,老舍更是“世界的老舍”。他在二十幾歲時走出國門,此后在歐洲國家教學、游歷達五年之久,又轉道南洋,在那里生活了大半年的時間。1946年,應美國國務院邀請,老舍和曹禺等人赴美國訪學,至1950年年初回到北京。這幾段異域經驗對于老舍而言意義重大。
在英倫期間,他涉獵了大量歐美古典文學和現代文學的經典作品,從古希臘的史詩到但丁的《神曲》,從狄更斯到現代派先鋒康拉德。30年代老舍在山東齊魯大學任教期間,開設了“文學概論”“歐洲文藝思潮”等課程,并撰寫了《文學概論講義》的課程講稿,可以明顯看到老舍是基于比較文學視野,對中國傳統文學和歐美文學資源進行比照、碰撞和整合,進而希望為創作實踐提供理論參照。

1963年,老舍(后排左三)看《茶館》排練后與主創人員交談。資料圖片
由此可見,老舍的知識體系較為完備,既有根底深厚的國學基礎,又有放眼看世界所獲取的西方文學知識和素養。他在不斷認識資本主義社會文化復雜性的同時,更迫切意識到“我們自己也是世界人,我們也是世界的一環,我們必須要使美國朋友們能夠真正了解我們的老百姓,了解我們的文化”。除了完成《四世同堂》第三部《饑荒》外,他還和翻譯家浦愛德合作,將《四世同堂》譯成英文,目的就是讓美國人民能夠了解到當時的中國人不再是唐詩宋詞里的傳奇,或是煙槍小腳式的“東方奇觀”,而是為了民族國家的尊嚴,犧牲自我、保全國家的抗爭者,也是可以殺身成仁、浴血奮戰的平民英雄。
相比較其他現代作家,老舍作品的海外傳播和接受程度非常之高,是作品被譯介最多的中國現代作家之一。20世紀30年代末,《駱駝祥子》就被日本和美國學者關注,并隨即被翻譯為日語、英語、瑞典語、法語、捷克語、波蘭語、俄語等。據不完全統計,迄今為止《駱駝祥子》已經被翻譯成二十余種語言。20世紀80年代,話劇《茶館》赴歐洲、日本、加拿大等地巡演,掀起了世界范圍的“《茶館》熱”,成為向世界講述中國故事的重要代表。由老舍作品的翻譯也衍生出近一個世紀的海外老舍研究熱。
巴黎第七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教授保爾·巴迪是法國當代老舍作品的重要翻譯者和研究者。他的博士論文就是以“小說家老舍”作為研究對象,認為老舍的作品表現出深刻而寬厚的人道主義精神,以及不為外在的理論框架所約束的獨立思考能力,在藝術上老舍還表現出以大量細節復現連續性的時代和社會生活場景的特點。巴迪教授的譯文和研究,引起了法國當代作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勒克萊齊奧的興趣。勒克萊齊奧認為,老舍是時代的表現者,他對當時北京城充滿矛盾和傳奇的呈現,讓人感受到狄更斯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神韻,在他身上最有力也最真誠地表達了“東方和西方相遇的必要性”。
值得注意的是,勒克萊齊奧稱老舍為“老師”,因為老舍對老北京富有質感、充滿細節的回憶,對經歷了巨大時代變動的北京城和北京人始終投射的溫藹、悲憫的目光,是最讓他動心的地方。透過勒克萊齊奧最擅長的家族敘事,我們同樣可以看到他將人物置身于時代變革的浪潮之中。這些人物并不局限在某個特定國家或民族,而是往往橫跨歐洲、非洲、美洲大陸,由一個家族敘事延展出一幅廣闊遼遠的世界圖景。小說《變革》中的馬羅家族經歷了近兩個世紀的革命與戰亂,由幾代馬羅家族人的眼睛,勾勒出跨越時空的時代動蕩與激變,也融通了整個人類社會對戰爭與殖民、暴亂與離散等相近的情感態度。透過勒克萊齊奧對個體生命在時代裹挾下的現實境遇和精神困境的關切,我們似乎能夠照見他所鐘愛的作家老舍的面影。
其實真正的經典作品是不需要被紀念的,譬如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歌德的浮士德、海明威的桑地亞哥、卡夫卡的格里高爾、魯迅的阿Q、丁玲的莎菲、沈從文的翠翠等,可以跨越時空、國別、民族的界限,融入每個時代不分畛域的人們的情感結構之中,毫無阻礙地成為當下我們施以價值寄托、精神訴求和理想追慕的對象。老舍書寫小人物精神困境的創作品格、立足于人道主義和人類情懷的文化批判意識,以及融通東西方文明、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的氣度,都足以作如是觀。